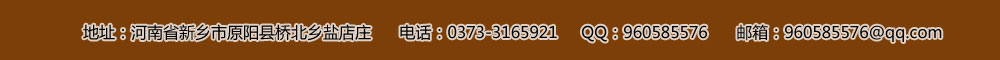东南亚南亚研究陈波藏文明与喜马拉雅区
二十世纪的西方人类学在研究藏文明时,受到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不能前往中国藏区进行研究,遂走向南亚,在那里寻找藏文明的替代者,有点类似研究汉文明的西方人类学家跑到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地区寻找汉文明的替代者。他们在南亚发展出两种想法:一种是以南亚的局部作为整个藏文明的缩影和代表,如南希在尼泊尔洪拉地区研究一妻多夫制,就带着不加区分的视角,将区域亲属制度视为整个藏文明的亲属制度;另一种人类学家则认为,虽然我不能前往西藏,但藏区的佛教是从南亚传播过去的,因此从源头研究藏文明及其地方化的过程就足够。这种观念体现在杰夫里的《文明化的萨满》一书当中。与此类似,中国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则基本上不考虑喜马拉雅山区国界线以外的部分,仿佛由于这条民族-国家模式的线在政治上具有隔绝作用,文明和文化的联系就完全不存在,在学术研究中也就完全不必考虑。这两方面的学者都受制于民族-国家的政治现实,而发展出大致相同的涉及藏文明的人类学研究模式。如何跨越这条线,更全面和客观地反映在这条线存在之前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成为今天研究喜马拉雅区域人类学的一个任务。
年的冬天,我从中国成都飞越喜马拉雅山,来到加德满都,在时任联合国驻尼观察团翻译官马克的帮助下,我在加德满都东区见到洛满堂王子晋美啦;在随后的接触和采访中,我逐渐走入这个王室家庭,访谈了洛域王国的最后一任国王晋美边巴(-)及其夫人,王子夫人等,从而略知王室的一些内况,尤其是最近四五十年的历史。
为了深入了解洛域王系及王国的历史,我们有必要回到他们的基本文化制度——藏系民族的亲属制度中去。
藏人的亲属制度、宗教制度与藏沛关系史在考察藏文明和沛域(大致相对于今日的尼泊尔加德满都一带)的关系历史时,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这个关系史类似于汉藏关系史。在藏史上,吐蕃帝国的开创者松赞干布曾娶过六个女子,其中一个即从尼泊尔来的赤尊公主。从亲属制度上来说,当时吐蕃和沛域之间已经形成甥舅关系。可惜由于缺乏文字的原因,这个关系及其历史呈现没有得到记录。但无论如何,建立在王朝/帝国之间的甥舅关系需要父系王系作为基础。
藏文明的亲属制度分布于两个区域,相应地有两种相辅相成的类型。中国藏区(即中国政治版图内各藏族居住区)的类型占主导,而西南区(包括拉达克、洪拉、多波和洛域,以及它们与阿里地区接壤的地区等)则为辅。中国藏区的亲属制度类型以双系继嗣和禁止血亲婚姻为主导,辅之以父系继嗣。在西南区则颠倒过来,以父系继嗣和交表婚占据主导,双系继嗣为辅。
这两种亲属制度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父系继嗣强调财产、地位/名号和家族等的传承,必须通过父系来进行。这就导致两种继嗣模式:长子继承制或幼子继承制。西南区尤其下部洛域的贵族家系,实行幼子继承制,而平民则是长子继承制。前者导致父系的大量财产通过嫡长子传递,而其他诸子则只能继承少量的财产,而不及父系的地位/名号和主干家族延续。只有当嫡长子在继嗣上出现问题而没有能力继嗣,或者被剥夺继嗣权以后,其下诸弟才有可能依序继嗣。幼子继承制与此相反,每一代人中除幼子以外,其他诸子都必须远离家系的大量财产、地位/名号和主干家系的承递。他们或者同地另建房屋居住,或者离乡,要么去别处上门,要么别立事业家室,要么继承家系在别处的产业,而不得在祖庭与幼子争嗣。无论如何,父系继嗣制对男性后代的要求非常严格。为了保证每一代都有男性后嗣继承和延续父系,人们在婚姻制度上采取很多的措施,譬如一夫多妻制。这种婚制常常是在前面的妻子无法生育男性后代时实践的。这种情况,在西南区的贵族家系甚至王系那里最为明显,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多见。但不能推论说,凡是有一夫多妻制的地区,其婚制的原因都是为得到男性后嗣。
在父系继嗣制中,女性后嗣相对来说不重要。她们要么出嫁他户,要么入寺为尼,要么终生独身。出嫁时的嫁妆也是金银珠宝、衣饰等,而无权及于父系的房产、土地、地位/名号等,更不用说父系的延续。如果父系绝嗣怎么办?只有在这个时候,母系的作用才体现出来。这时由女儿(依序)负责财产、地位/名号和家族等的传承,招赘上门,生儿育女;但下一代仍然回到男性继嗣。母系继嗣是在父系继嗣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补充。
父系继嗣常常是和交表婚连在一起。交表婚简单说来就是兄/弟的子女和姊/妹的子女之间通婚,对具体的个人(Ego)通婚来说,又涉及到母亲一方(譬如母亲的兄/弟的子/女)和父亲一方(譬如父亲的姊/妹的子/女),有的某方(譬如来自母亲一方的表亲)有通婚优先权,有的没有。西南区属于没有优先权的情况,比如洛域的当地人称“阿妮(姑姑)阿相(舅舅)的孩子”可互相通婚。从财产的意义上说,这种婚制一定程度地将财产流动维持在亲属范围以内,换句话说,叫财产不外流,当我们把这一点跟中国藏区的理念和实践相比较时尤其明显。
中国藏区基本上禁止在血缘亲属之间(藏语称宾家,spun-ca)通婚,而且是双系的血缘亲属都包括在内。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非常小心地将他/她的各个亲属指认给他/她,那都是不可通婚的范围,以免将来闹出麻烦。他们的婚姻对象必须要在血缘亲属之外去寻觅。这造成一个什么后果呢?那就是从财产、地位/名号和家族传承等的意义上来说,中国藏区模式始终是向外来者开放的。在财产、地位/名号和家族等的继承上,则是双系继嗣,即后嗣男女都能平等地继承,没有性别上的歧视;家系也不重视父系的传承。非但如此,笔者还常常接触到这种情况,即一家之中,若后嗣中有女子若干,男子若干,男子则要么入寺为僧,要么入赘他户,要么娶妻另建房屋居住,而把祖庭留给自己的姊妹,由她们(依序)招赘,负责财产、地位/名号和家族等的传承。男女平等,造成男性后嗣可以四海为家,而不局限在父系内承继祖业。换句话说,在前一种亲属制度下,不同群体之间交换女人是常态;在这里,不同群体之间交换男人成为常态。在双系继嗣和双系婚姻禁忌的情况下,人们心性豁达,心胸开放。
比起西南区的父系继嗣、内地汉族古代和至今许多地区的父系继嗣和男尊女卑、南亚至今仍普遍的重男轻女(仍然是父系继嗣)传统来说,这不止是一个另类的性别关系模式,若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说,他们还走在这些区域的前头。
不过,在中国藏区,吐蕃时期的王系、后来各地土司的传承,则是父系的。如果他们的父系继嗣绝嗣,也可以像西南区那样招赘,也可从外面过继男子。
历史上,藏区的权力模式基本上由两种类型构成,一种是赞权制(来自赞普的权力),一种是活佛制。从时间上来说,王权制早于活佛制。吐蕃王系就是王权制的典型代表。王权制的基础是父系继嗣,或者说它是父系继嗣的政治延伸。敦煌文献记载的吐蕃王系是父系继嗣的,而且它是外来的。后来九世纪吐蕃帝国中央集权分崩离析以后,由吐蕃王系派生出来的各地的地方王权仍然延续相当长时间。这种权力模式在元以后各地的土司政权中得到继续。
西历十世纪以后,佛教经过一个多世纪和本土文化的互动、互相吸收等有机的衔接,逐渐占据藏区的主要政治舞台。赞普继嗣的父子相继模式撤退后留下的大量空间,逐渐为藏传佛教中的师徒关系所填充。这种关系比父子关系还要重要,许多师徒关系就隐喻为父子关系,但这种模式在权力和法统传承上,尤其当它面对活佛制时显得脆弱不堪。外来的佛教和本土文化结合的最大成就,乃是活佛制的政治形态。它以上述藏族的双系继嗣和血亲婚姻禁忌为基础,或者说它是这种亲属制度的政治呈现和宗教制度呈现。萨迦派在元代获得蒙古帝国的支持后,一时显赫。不过,在权力模式上,萨迦派给我们提供的不仅是一个历史概念,而且是一个类型概念。如果藏文明主要的权力模式是王权制和活佛制的话,萨迦派的实践就是二者的结合:既有元宫廷下嫁公主与萨迦世系,其喇嘛也负责管理天下释教。
基于藏文明亲属制度的这三种权力模式,对藏沛关系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赞普权力制在中心藏区的消失,导致吐蕃和沛域之间的甥舅关系的消亡。其次,萨迦的政权模式在元以后向吐蕃西南方向扩展,并进入喜马拉雅山区及以南区域。甥舅关系在嫁娶的方向上发生变化,成为舅甥关系。第三,活佛制在喜马拉雅地带(包括南麓)大量扩展。这三种关系在时间上前后相继,但后两种关系后来并存,一直延续到今日。
卡萨帝国、洛域王系与舅甥关系西历九世纪以后,统一的吐蕃帝国崩溃,吐蕃王系星散,形成各地方王系。其中吐蕃帝国最后一任帝王朗达玛,其大妃生子云丹,分布于隆雪、彭域和多康等地。朗达玛小妃之子为沃松,其一孙尼玛衮时抵达阿里普兰建尼松宫堡,其长子据芒域,次子据普兰,幼子据祥雄。是为阿里王系之始。另一孙赤扎西孜巴贝后来发展出宗喀王系(青海西宁一带)和雅砻王系。又有亚泽王系,系君王赤德之后,发展出后来的卡萨帝国。
西历十三世纪上半叶,藏西芒域的贡塘王国开始扩展并在阿里地区迅速强盛起来;年,贡塘国王衮布德(mGon-po-lde)和阿里的卡萨(Khasa)国王茶卡拉(Kracalla)之间发生战争,贡塘国王兵败吉隆被杀。一时,阿里地区、洛域,喜马拉雅西部的山地区域库冒(Kumaun)和噶瓦(Garhwal),和尼泊尔西部都被卡萨王国所统治。可是不久,贡塘王国后嗣和萨迦政权的昆式家族联姻,在后者的影响下,贡塘王国随后打败卡萨王国并重获贡塘核心区域的统治权。但卡萨王国早期在这一区域的扩张和宰制权并不因为区域的小败而受到挑战。它一直延续到该世纪末。蒙元帝国建立后,通过萨迦班智达的作用,西藏成为元朝的一部分。萨迦派获得朝廷的大力支持,随之,贡塘王国也受益,并在萨迦世系和朝廷的佑助下,经过第二次贡卡战争,迅速成为阿里地区的强大政权,统治了洛域、多波(Dolpo)、尼乡(Nyeshang)、玛囊(Manang)、廓尔喀北部和吉隆等,并在各地的战略要地建立十二个城堡,一时无人能敌。后四个地区都在喜马拉雅山南坡。贡塘国王赤德崩(Khri-lde-‘bum)甚至前往元朝内地,得到元廷皇帝的支持,他随后在藏西十三区建立起强大的政权。与此同时,他继续其祖父时代开始的和萨迦世系联姻的传统,娶萨迦统治阶层的桑布白(bZang-po-dpal,-)的女儿。甥舅关系在喜马拉雅西部区域的不同王国之间确立。
第二次贡卡战争时,卡萨国王阿索卡卡拉(Asokacalla,c.-)在位,他死后其子智达墨(Dzi-dar-smal)嗣位,开始在喜马拉雅山区域向东向南扩展,一度逼近贡塘掌控的多波和吉隆之间的区域,并在年、年和年,三次进入加德满都河谷地带。大约-年之后,萨迦内部争夺,开始衰弱,无法继续提供支持。年,萨迦政权内部四个拉章分裂,势力更削弱。尽管贡塘和萨迦拉章之间的关系仍然延续,但贡塘势力亦随之稍衰。
年,卡萨帝国在国王日普马拉(RipuMalla)率领下,又进入加德满都河谷。卡萨一直支持的是直贡嘎举,和蒙古人的关系也一直不稳定。随着东扩,它试图寻求和萨迦政权改善关系。在国王吉他里(Jitari)时期他派自己的次子阿迪提亚(Aditya)前往萨迦寺学习佛法,希望通过这个联系改善和萨迦统治者的关系。此举确实结束贡塘独占和萨迦联姻带给贡塘的好处。阿迪提亚学成后回去娶妻嗣位,他后来派自己的孙子普拉塔巴(Pratapa)马拉前往萨迦寺削发为僧。年和年,卡萨势力再次进入加德满都,阿迪提亚要求加德满都国王按其父时的约定上贡。此时,它似乎已经从贡塘手中收复洛域、多波、玛囊,尼乡,奴日(Nubri),瑞(Rui)、聪(Tsum)和吉隆等整个区域。他建立起藏卡(卡萨语,即旧尼泊尔语)双语统治。年,阿迪提亚去世。他的女婿、普兰地方的首脑索朗德(bSod-nams-lde.c.-)前来继任王位,在他及其子皮提夫(Prthvi)马拉(c.-/)治下,卡萨王国进入一个强盛时期。由于普拉塔巴入位为僧,于王权无兴趣,索朗德和王后萨坤纳马拉(Sakunamala)公主扮演国王施主(尼语danapatimaharaja)的角色,向萨迦寺布施,为萨迦班智达的宝座供奉金伞盖。年,索朗德重新控制整个尼泊尔东部,成为喜马拉雅区域的一个强大帝国,此即卡萨帝国全盛时期,其版图从尼泊尔东部山谷向西,一直拓展到克什米尔以西地区,北起雅鲁藏布江(即布拉马普特拉河),南至恒河的广大区域。洛域此时置于他的治下。他的儿子执政时,还向拉萨的千手千眼观音供奉,确立施主-喇嘛关系。
十四世纪中叶,萨迦政权由于内部激烈的内讧,最终让位给东部的帕珠噶举。但它和贡塘之间的联系依旧保持着,不过贡塘和元廷之间的关系加强,并从后者那里得到大匀霞(Ta-dbun-sha)封号。尽管如此,卡萨王国的强盛使它失去南部的区域。年,元朝的统治被明朝取代。贡塘王国失去两个重要的支柱。
卡萨大臣班丹扎巴很可能是皮提夫的女婿,皮提夫死后绝嗣,他开始实际掌政。王系缺乏男性继嗣,这种状况造成帝国统治家族内部的权力争夺。各地诸侯(在尼泊尔西部就有五十个)自相雄长。卡萨帝国瞬间崩溃。贡塘国王索朗德(c.-)迅速夺回对喜马拉雅区域的控制,包括洛域、普兰、多波、玛囊、奴日,甚至还可能包括吉隆。帕珠政权则夺回对阿里大部分地区的控制。
贡塘王国派出长官治理洛域。随着贡塘王国和卡萨王国的式微,洛域长官逐渐享有自治。年,第三任世袭洛域长官阿妈贝宣布脱离贡塘王国,自我管理,从此一直传至今日。此后的漫长历史,对洛域来说,也充满斗争。其中俊拉王国取代卡萨帝国、上下洛域的分离、洛域与廓尔喀结盟在十八世纪并随后归属于廓尔喀王朝,是最重大的事件。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末,洛域都是在险境中求生存,其中包括多次被峻拉王国征服,课以重税;年,因廓尔喀人西进,欲图连接峻拉王国周边的势力以对付该王国。洛域已经遭受峻拉王国的欺凌和苛捐杂税的盘剥。廓尔喀的战争对手是峻拉王国,廓尔喀将军的策略是尽可能地孤立它,建立反峻拉的统一战线。他派人前往洛域游说,许诺只要洛域加以援手,灭峻拉以后,洛域归附廓尔喀,每年只需交纳卢比和5匹马的贡赋便可,其他内部事务廓尔喀朝廷一概不过问。洛域王国权衡利弊,同意了,从此洛域并入廓尔喀王朝。中尼双方都正式认定从这一年开始,洛域归入尼泊尔王国的版图。沛域作者饶密西对此归入,喜悦之情跃然纸上:“在此后20或30年的时间里,除了每年朝贡卢比和5匹马,木斯塘相当自由,不再有其他的责任。”“因此,木斯塘作为一个依附邦,其主要的责任乃是负责处理其北部边界的问题,并在无论何时和必要的时候为尼泊尔提供其全部人力。”“除了其对尼泊尔的军事承诺,木斯塘尽情享受新获得的自由,免受税收、费税和征收的盘剥。每年给峻拉王国的朝贡卢比和5匹马是确定的;但实际上,峻拉王国随意增加征收费税。峻拉王国的权威包括国王们和皇家的成员,一度经常到木斯塘去进行节庆的访问,这更增加了对木斯塘的盘剥。到大约年代或年代早期,峻拉王国还夺走了木斯塘差不多70%的主要的朝贡领土,包括所有下部木斯塘的贸易和关税中心。因此,每年向尼泊尔朝贡卢比和5匹马,但却能实在地享受祖先曾掌控过的区域上的权威,对木斯塘国王来说,这实在是一个伟大的收获。”这段分析有两点值得白癜风怎么引起的云南儿童白癜风医院